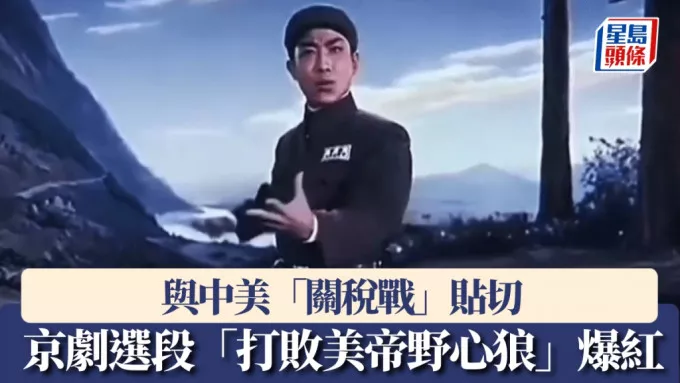山西“订婚强奸案”二审宣判:两个问题引发争议
来源:倍可亲(backchina.com)被网友称为“订婚强奸案”的山西大同席某某案,今天(16日)上午二审宣判。
据悉,该案刑事、民事二审均裁定驳回上诉,维持原判。此前,该案被告人席某某一审以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。
“法度law”注意到,该案定罪核心争议在于是否存在违背意志的插入性行为。有文章认为,审判长强调“处女膜完整性不影响强奸认定”,刻意回避了生物物证缺失及事后清洗的孤证困境。
生物物证缺失包括被害人阴道擦拭物未检出男方DNA,且床单精斑仅能证明性接触,无法直接证明插入行为。对“性行为必然导致处女膜破裂”的否定,并不能反向推导“插入行为必然发生”——二者在逻辑上非充要关系。
而事后清洗的孤证困境则指:法院以“被害人陈述洗澡”解释DNA缺失,但未提供浴室使用记录、水痕检测等客观证据佐证,该陈述仅属单方口供,存在虚构可能。
此事引发广泛争议。北大(专题)法学院教授陈永生认为,审判长声称床单上检测到精液,但是被害人体内没有检测到精液,而且处女膜完整,二审法院居然维持强奸既遂的一审判决,太荒唐。
此外,该案审判长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一段话也引发争议。
据媒体报道,该案审判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:席某某的母亲作为辩护人,多次擅自把涉及被害人个人隐私的信息发布到网上,侵犯了被害人隐私权,二审期间法院依法对其进行了训诫。与席某某家人主动爆料接受采访、形成不对称舆论所不同的是,被害人选择相信法律,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谢绝所有上门媒体的采访,拒绝舆论炒作。
对于上述采访内容,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何兵认为:“法官判决后,不应对媒体评论案件。最高法院的法官职业伦理规定,有明确条文约束。这种公开评论,使得法官成为自己判决的辩护人。法官判决以后,必须对媒体保持缄默。判决是法官的权力,评论是社会的自由。”
资深刑辩律师周立新对“法度law”表示,“法官在判决以后还要对自己判决的案件公开做解释,那只能说明他的《判决书》理由不充分,道理没讲清楚。另外,办案法官的身份,正如何兵老师所说,他的所有话只能体现在判决书中。”
媒体此前报道,2023年5月1日,山西大同市阳高县27岁席某某和24岁女子吴某某举行订婚宴,双方签订《订婚收彩礼协议》,男方当天给女孩一半彩礼10万元和一枚7.2克的金戒指,承诺结婚一年后,在90多平方米的婚房房产证上加上女生名字。5月2日下午,两人在婚房发生关系后,女方控告男方强暴。
2023年12月25日,阳高县法院对该案刑事部分作出一审判决,席某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,席某某当庭上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