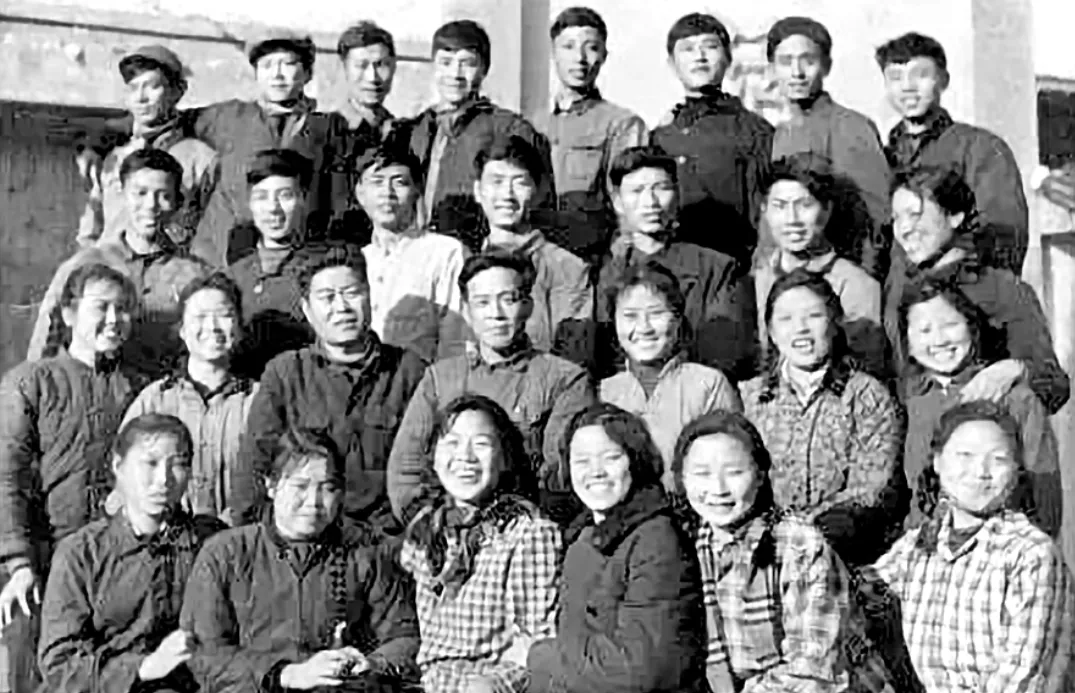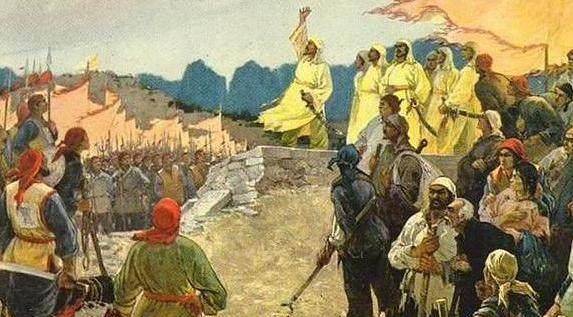活人也要破地狱
来源:倍可亲(backchina.com)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,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,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。但暗夜又在那里呢?现在没有星,没有月光以至没有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;青年们很平安,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。
绝望之为虚妄,正与希望相同!
——鲁迅,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
用当下的话来说,那就是:
活人也要破地狱。
他叫阮籍,魏晋风度代言人,竹林七贤之一。
他在世的时候,人们就说他狷狂旷达,好像名士都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。
其实,没有几个人懂他。
他只是故作狷狂,故作旷达。他的内心十分苦闷,十分悲痛。
他时常驾着车子,狂奔在遍布荆棘的岔道上,直到巍峨的高山挡住了去路。
马儿失蹄,车轮打滑,他再也冲不过去。
无路可走,他颓然痛哭而返。
一个没有出路的中年人,在乱世的落寞形象,莫过于此。
隔着一千多年的时光看魏晋,我们总以为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。但阮籍用他的颓废,用他的焦虑,否定了这种错觉。
魏晋易代之际,从名士开始站队,顺我者生,逆我者死。
他是曹魏政权的拥趸,面对司马氏的咄咄逼人,若不想死,该如何自处?
于是,他的一生似乎都在醉着。
醉酒,是一种逃避,也是一种对抗。
他有一次听说步兵校尉厨中有三百斛好酒,便主动向司马昭要官。
上任之后,真的就是喝酒,没日没夜地喝。
司马昭想和他结为亲家,他不愿意,又不敢直说,就喝得酩酊大醉,一连醉了六十天。
故意搞得司马昭连提亲的机会都没有,只好作罢。
司马昭晋封晋王,想借用他的名气,要他写劝进文。
他不想写,又不敢推掉,于是又喝得大醉。
这次没能躲过,人家把他弄醒了。
他没办法了,提笔一挥而就,写了一篇富丽堂皇的劝进文。
但他不忘在文章里挖坑埋雷,搞弦外之音。
诗,和酒一样,也是他表达苦闷的方式。他写了好多五言诗:
夜中不能寐,起坐弹鸣琴。
薄帷鉴明月,清风吹我襟。
孤鸿号外野,翔鸟鸣北林。
徘徊将何见,幽思独伤心。
在他之前,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人生写得如此孤独,如此悲凉。
他的内心跟嵇康一致,但没嵇康那样刚烈,缺乏正面斗争的勇气。
所以,他在沉重的现实里追求思想的自由,灵魂显得更加的痛苦。
他看不惯小人,尤其看不惯伪君子,就写文章讽刺,以隐喻的形式:
群虱之处乎裈中,逃乎深缝,匿乎坏絮,自以为吉宅也;行不敢离缝际,动不敢出裈裆,自以为得绳墨也。
什么意思?
他不敢直接骂儒家的伪君子,故而用虱子比喻这帮人,说虱子在裤裆,躲在深缝里,藏在坏絮中,自以为住的是豪宅;走路不敢离开线缝,行动不敢跑出裤裆,自认为很守规矩。
他是个大孝子,很爱他的母亲。但在母亲的丧礼上,他偏偏不哭,甚至喝酒吃肉。
等到吊唁的宾客都走了,他想起来很悲痛,大声嚎啕,连连吐血。
他以青眼白眼看人生。
对待俗人,他就翻白眼;接待知音,则青眼有加。
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,所谓的狷狂,成了他的外壳,用以保护他内心的真。
他叫李贽。54岁那年,他辞官了。
起因是他在云南姚安的知府任期将满,上级官员要向朝廷举荐他升官。没想到,他一听到升官的消息,拔腿就跑。
他是一个真实而坦荡的人,直言做官只是谋生的手段,只是社会职业的一种,从不去夸夸其谈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。
嘴上不说,他却比空喊口号的官员清廉得多,口碑和实绩也都好得多。不愿同流合污,坚守内心孤傲,是他20多年官场生涯痛苦的根源。
做官期间,他处处与上级领导“触”。
这种抵触未必是行动上的抵牾,但其内心有棱有角,与现实格格不入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合群是合群者的通行证,孤独是孤独者的墓志铭。
为了承担家庭与家族责任,20多年里,他不得不收起触角,摸黑前行,孤独痛苦,难以言表。
一个中年人,肩上有太多的重担,内心有巨大的压力,他只有默默忍着,不敢出声,尤其不敢顺从自己的个性,好好任性一把。
再苦再累,再泯灭个性的光辉,也只有咬牙坚持。哪怕牙断了,只能和血吞。
他始终清楚,一个中年人活着的意义——为妻子而活,为子女而活,为父母而活,为家族而活,唯独不曾为自己而活。
这期间,中年李贽经历的苦难一点点磨砺他的本性,也一步步释放他的枷锁。
因为清贫,他有过极其深刻的挨饿体验。
他的至亲,包括他的父亲、祖父、儿子和两个女儿,在几年内陆续去世。那段时间,他说与妻子黄宜人“秉烛相对,真如梦寐”。
生命中有太多无法承受之重。连李贽都只能把这一连串的重击当作梦一般,以此麻痹自己的内心。
54岁,在绝大多数人一眼望到死亡的年纪,他却辞官重新出发了。
去寻找他渴望了大半辈子的独立、自由与个人主义。
从选择落脚的地方,他就表现得与众不同。一般官员都是告老还乡,发达不还乡,如锦衣夜行,成功了也没意思。
而李贽,没有选择回老家泉州,却去了湖北黄安,寄居在耿氏兄弟家里。
他的理由貌似很纯粹,因为这里有朋友,生活不用发愁。
“我老矣,得一二胜友,终日晤言以遣余日,即为至快,何必故乡也?”他说。
事实上,他不愿回老家泉州,与他的个性有关,他平生不爱被人管:
人生出世,此身便属人管了……入官, 即为官管矣。弃官回家,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。来而迎,去而送;出分金,摆酒席;出轴金,贺寿旦。一毫不谨,失其欢心,则祸患立至,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,管束得更苦矣。我是以宁飘流四外,不归家也。
这个理由,与他辞官时所说“怕居官束缚”是同样的道理,都表达了一种对独立、自由与个人主义的渴望。
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说,按照当时的习惯,李贽一旦回到泉州,他所需要照顾的绝不仅止于自己的家庭。
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,又做过知府,那就一定会陷入无数的邀劝纠缠之中而不可自拔。
然而当时的李贽,已历经生活的折磨,同时又研究过佛家和道家的思想。他在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,重建人生观之余不能再墨守成规。
也就是说,他不能把读书、做官、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,也亟待摆脱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。
可以看出,李贽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。
他标榜个人价值,企图挣脱一切宏大意义,既不能受缚于官僚体制,亦不能被传统的家族观念困住。
他选择了一个远离故乡,远离宗族的地方,作为终老之地。
他早看透了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族之间的感情虚伪,在世人面前假哭,以维系所谓伦理关系,目的则是为了争夺财产继承权。
62岁那年夏天,他在寄居地湖北麻城维摩庵剃去头发,却留下胡须,成了个亦僧亦俗、不僧不俗的模样。
朋友见了,都很惊讶。他淡定地解释说,天气太热。
不过,他剃发的真实想法,在另外一些场合,坦率地表达了出来。
他在一封信里说,之所以落发,是为了对抗家族俗事,让家族中人彻底死心,不要指望他还能回去。
在给知交焦竑的信里,他说得更决绝:
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,共以异端目我,我谓不如遂为异端,免彼等以虚名加我,何如?
反正世人都说我是“异端”,我干脆就剃个光头成全他们,怎样?哈哈。
他叫朱耷。他有个更出名的外号:八大山人。
朱字去掉“牛”为八,耷字去掉“耳”为大,故而此次易名是去掉“牛耳”之意。
牛耳,指的是在某方面居于领袖地位的人物。失去“牛耳”,沦为牛马。
除此之外,他还用过一堆外号,每一个都很不把自己当回事。
比如雪个、个山、个山驴、驴屋、驴……
这到底是怎样一个丧气逼人的人物,才能如此怡然自得地自嘲?
其实,他出身显赫,是朱元璋的十世孙,典型的皇室血统。
但是,在他18岁,举行成人礼的年纪,大明亡了。
然后就是父丧妻亡,一个人能经历的家国沉沦,他都经历过了。
崇祯帝上吊后,所有人都以为明朝的历史已经写完。只有活着的子民,才知道这不过是翻页而已。
俗世已经留不住朱耷了,他遁入空门。
他用一支画笔,聊遣余生,达到了人画合一的境界。
他的画,极简。
通常是一张白纸,两三笔,甚至两三个墨点就完成了。
最显著的标志,是他画出来的眼睛。
无论是一条鱼,一只雁,一只凫鸟,眼神总是似睡非睡,死气沉沉。
他笔下的活物,已然不是活物,而是一种生命的苍凉。
它们翻白眼的时候,就像他对待世界的态度:
时代予我痛击,我报之以白眼。
他堪称中国版的甘地。
我既然无力反抗你的统治,我选择非暴力不合作,不行吗?
清代鸡汤文大师、《幽梦影》作者张潮,写过八大山人的逸事:
予闻山人在江右,往往为武人招入室中作画,或二三日不放归。山人辄遗矢(屎)堂中,武人不能耐,纵之归。
总有一些附庸风雅的人强行把他请到家中作画,一画就要好几天,山人不爽想怠工,就在人家客厅里拉翔。
结果,如愿被轰出来了。
这画风,跟唐伯虎有得一拼。当年,唐伯虎得知宁王朱宸濠蓄意谋反,遂装疯卖傻,公然裸露下体,宁王受不了,放他回老家了。
总之,八大山人的人生态度,丧到了极点。
他说自己“墨点无多泪点多”,悲伤无以名状。
这个老头,都认识吧?
曾国藩,功业很大,名头很响。很多人以他为终生的学习榜样,但很少人知道,他简直就是悲剧的代言人。
与阮籍、李贽和朱耷不同,他的悲哀没那么抽象,而是具体可感:
考试挂了,今天很丧;生病难受了,今天很丧;打败仗了,今天很丧……
30岁以前,他基本是个平庸之辈,且一直在怀疑自己的智商。
他似乎遗传了父亲的基因,就是读书不咋滴。曾家的孩子都这样。
他后来说,几个兄弟中,除了老六曾国华比较聪明,其他诸弟“天质较低”,有的比他还愚笨。
他本人考了七次,才勉强中了个秀才。
其中第六次考秀才,主考官在他的试卷上批了十个字:子城(曾国藩原名子城)文理欠通,发充佾生。
佾生是祭孔用的乐舞生。这相当于说,就你这点儿分数,去做个艺术生差不多。
“艺术生”后来走运,竟然考了个“同进士出身”。但,这并不表明他的生活就很励志。
他的人生态度,一如既往的丧。在日记中刻了个“早”字。然后,就没有然后了,照常睡到天昏地暗。
他曾休假四十多天,在这四十多天里,写了几封家书,作了一篇祝寿文,其余时间全在喝酒、应酬、吹牛逼中度过,导致天天没东西记日记。
做京官那会儿,他的理想是外放。但不是做督抚之类的封疆大吏,而是做个学政或主考之类的小官员。
目的也不是为了成就什么大功业,而是学政或主考是肥差事。这样,他就可以不用天天哭穷。
他希望得到江西主考的差事,结果被别人得了去。于是,很郁闷地写信说:
真不知道做官有什么意思。
后来,在与太平天囯的生死搏斗中,他基本上一吃败仗就想到自杀。真是丧得不要不要的。
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,已经位极人臣的他,终于,终于……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意趣。
这时候,身体多病,让他的人生不丧都不行。
他是个典型的“药罐子”,一生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与病魔作斗争。
35岁起,他得了牛皮癣。此病特难缠,几乎伴其终生。
每当军事不顺,身上就奇痒难耐,以至于搔得全身上下出血不止,痛苦万分,只觉“无生人之乐”。
他的日记中,“遍身疮癣,且痛且痒”的记载不可胜数。
晚年,耳鸣、失明、失眠,各种病魔折磨着他,让他生不如死。
他常找弟子赵烈文倾诉,动不动就说“唯祈速死”。
更悲剧的是,他看不到自己效忠的王朝,前途何在。但他老了,不可能再肩负起“挽狂澜于既倒”的重任。
他明白自己已落后于时代,不再属于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。但他,又不愿消极地等待时代的淘汰。
所以,他给自己写了一句自勉的话:
禽里还人,静由敬出;
死中求活,淡极乐生。
意思是说,修行好的话,禽鸟也能投胎成人,想内心平静,先要敬重周围的人事。死中求活,在绝境中不放弃希望,看淡一切功名,才能享受人生。
这样的曾国藩,让人莫名感慨。
看到这里,你以为他们活得如此不堪,活得万念俱灰,就一无所成了吗?
身为乱世中的名士,阮籍只想做个普通人,路人甲。
他不想,也不敢跟着嵇康做烈士。
狷狂,于是成了他最好的保护色。
他成功了。
嵇康死的光荣,阮籍生的伟大。
他留下了伟大的诗歌,生命的色彩,以及温柔反抗的技术。
李贽活成了生命可以苍老,思想绝不苍老的歌者。
他的狷狂性格,是对世俗人生的反叛,也是对传统礼俗的抗争。为此,他不惮与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为敌。
晚明,一个走向没落衰颓的时代,竟是这名执着的老者,为帝国涂抹了一笔最有力的青春色彩。
他做的第一件石破天惊的事就是,把孔子请下神坛。
他告诉世人,“圣人不曾高,众人不曾低”。
他否定孔子、孟子的圣人地位,认为孔孟非圣人,也和常人一样,两者没有高低之分,所以人人皆可成圣,没有必要以孔孟的是非观作为自己的标准。
他说,道路不只有一条,心性也不只有一种,怎么可以强求同一?
他批判程朱理学,指出所谓正统人士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,志在巨富。
他极其痛恨那种“阳为道学,阴为富贵,被服儒雅,行若狗彘”的伪道学家们。
他认为“人必有私”,人人都有私心,孔子也不例外。
他其实是一位真正尊崇孔子的儒生,所以要让孔子回归到人本身,拒绝程朱理学对孔子的神化,更反对统治者利用孔子来钳制人性,禁锢思想。
他说得很直白:“穿衣吃饭,即是人伦物理;除却穿衣吃饭,无伦物矣。”
以此,将程朱理学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那一套束缚性的礼教击打得粉碎。
不仅如此,他还公开挑战男女大防,给男权社会难堪。他为女性说话,说头发有长短,但男女的见识无长短。
他几乎把人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彻底翻了个个儿。
他干过的事儿,300多年后,五四时代那些反传统的知识精英照着又干了一遍,然后一个个成为了启蒙大师。
而朱耷,这么丧的一个人,竟然没有郁郁而终。
他活到了80岁,而且功成名就。
清初以后的画家,都得承认他的江湖地位。他的任何一幅画,现在都值一线城市好几套房。
他的影响早已超越国界。
1960年代,美国一帮后现代艺术家看了他的画,惊异于300多年前中国画家的表现力,进而开始探索自己绘画的变化。
所以,他的负面情绪,其实隐藏着极其正面的人生态度。
就像他的落款“八大山人”,在书写上,总是可以呈现出“哭之”“笑之”两种形态与理解。
至于曾国藩,更是用一人之力把人生之苦提升到了成功学的高度。
他从穷乡僻壤起步,在一无家学、二无家族背景的情况下,一路丧下来,竟崛起而成“晚清中兴第一名臣”。
他获评的名头都很吓人:旷代圣相、古今第一完人、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圣人……
有人说,曾国藩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证明:一个资质平平的人,在意志力的推动下,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。
真正绝望的人生,是无声的。绝望者的声音,谁也听不到。
面对生活中的郁闷和暴击,我们也许会想起阮籍,也许会想起李贽,也许会想起朱耷,也许会想起曾国藩。
他们教会我们的人生哲理,用来对付日常的愁与苦,不多不少刚刚好。
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。你要么让它变得更好,要么让自己变得更好。
这就是活人的破地狱。